
1
春节那几天,我父亲回老家见亲戚,和我的几个表哥吃了顿饭。酒过三巡,我小姨父出现在酒桌上。没有人记得曾经邀请了他,所以他的到来有些突兀。酒桌上的氛围一时间落到了冰点。我父亲倒了杯酒,摆在小姨父的面前。他小口小口,慢慢饮尽,但刚喝下去的酒,仿佛又从眼眶里淌了出来。他看着一桌亲戚,捂着脸说日子过不下去了。
他说,欢华走了以后,我的日子不好过。以前是她给我洗衣拖地,现在我一个人,饭都不知道怎么做。每天起来,一个人从早坐到晚,就坐在山上的柚子树下,张口向天,柚子也没有掉一颗下来。
他们就一起沉默。
欢华是我小姨的名字。她于去年八月初去世。
小姨父坐在春节的酒桌边絮絮叨叨说了一些话,我父亲带着几个表哥跟着点了点头。小姨父起身抖抖衣服走了。他走之前还从桌上拿走了一包烟。大家都看到了,但没有说话。小姨父离开有一阵子之后,他们都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,于是重新开始聊天,劝酒,划拳。有人从口袋里摸出一包一模一样的烟,摆在桌上同样的位置,先前给小姨父让座的某位表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新坐了下来。
不避讳地说,我父母辈的亲戚们对小姨父曾经是很有微词的。我从很小的时候,就听见他们在安静的地方小声嘀咕,说我这个小姨父好吃懒做、当大爷、好酒、好赌、打老婆。他们说得最多的,是他命好,找了欢华当老婆。据说我外公外婆当年是有意见的,但我小姨父找准了我外公的弱点,带了两瓶酒上门,最终把我小姨讨回了家。
他们说这些的时候,我还只是个孩子,我父母辈也不过是我现在的年纪。当我不再是个孩子时,他们偶尔也会说几句,但更多时候都不再把话题往那个方向引。我知道这当然不是我小姨父变好了,而是我小姨在家族的视线里越来越淡。
我母亲有三个姐妹,两个哥哥,小姨是老来子,六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那个。俗话说,“皇帝爱长子,百姓爱幺儿”,但我小姨似乎没有得到多少父母的爱。她没有读什么书,主要在老家务农,去过最远的地方大概就是南昌,不是来看我妈妈,就是来看病。
她也不是没有机会离开故乡,只是当时来说并不算大的年纪,离开了故乡,就不习惯。大姨的女儿,只比小姨小五岁。四十年前,大姨在南昌工作,到了周末,外婆就用一根扁担两只箩筐,挑着表姐和小姨乘船去看女儿。那时候的小姨虽然辈分比我表姐高,但身体却比表姐还要瘦弱。外婆的扁担前头挑着小姨,后头挑着我表姐,离码头还有十几里路,天上下起雨。外婆打开雨布,一块盖在前头,一块盖在后头。小姨开始在雨里哭,表姐裹着雨布,好奇地探头向箩筐外看。
过了几年,表姐也去了外地工作,她在码头坐船,小姨跟在她身后哭,拉着她的衣角,一路跟到了船舷边,就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。
母亲不止一次说,小姨就是老实,但又不是那么老实,她胆子小,不敢出去闯,但在家里很机灵,顽皮起来谁都管不住,读书的时候就知道爬树掏鸟蛋,老师出去上个厕所,回来就看不见人了,也懒得找。她就挂在树上,一只手扳着树杈,一只手磕开鸟蛋往嘴里倒。喜鹊就站在旁边的树枝上,喳喳冲她喊。
小姨还是个孩子时,外公外婆起早贪黑下地挣工分。家里的事情,长兄为父。我大舅舅管起妹妹来,比他的父母凶得多,不好好读书,就折树枝抽打。我母亲怕他,但小姨不怕,因为我小舅舅喜欢小姨。我小舅舅会为她穿衣服、送饭、洗脚,甚至替她挨打,从小如此。
每次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,小姨吓得天色昏黑都不敢回家,大舅舅会横一张长凳在家门口,长凳边斜靠一支竹枝或柳条,端着一搪瓷海碗饭,盯着门前那条隐没在夜色中的石板路,凶狠狠地咀嚼。而我小舅舅就会翻出院墙,绕一个很大很大的弯,去小姨躲藏的地方,给她带两个馒头,或者一只烤红薯。
后来我大舅舅去县里工作了,大姨和二姨去了南昌,又去了更远的地方。几年后,我母亲考上了南昌的学校,小姨和小舅舅两个人在老家陪父母。
再之后,小舅舅也去了外地,辗转走过很多地方,小姨还是留在了老家。
很多时候,我父母的讲述就会停在这个部分,他们很少会继续讲在那之后小姨的故事,似乎小姨在那之后就成了一个没有故事的人,在老家,陪着我的外公外婆日渐衰老。
2
小姨上次来南昌,大概是十几年前。那时候,我在上大学,回来看见紫色面膛的小姨,有些吃惊。她对我笑,脸上的皱纹有些多,不知道是灰尘还是岁月,把她的脸捏成了皱巴巴的样子。
母亲告诉我,小姨会住一段时间,争取找一份工作。她不喜欢上楼,就收拾出了储物间,安好了电灯,搬进去了衣橱和单人床。母亲很愧疚,放东西的房间拿来住人,还是自己的亲妹妹。小姨嘻嘻地笑,说那有啥嘛,住得很舒服了。
那时候的我很畏惧和亲戚们来往,打过招呼,就躲进自己的房间。我看小姨时是嗫嚅的,小姨看我时会很兴奋地喊我的名字,然后也喃喃地欲言又止。这时候的小姨,和在老家的小姨,如果不是她喊我名字时的兴奋太熟悉,其实就是两个人。
我没有在家里待多久,就回学校了。再从学校回来时,小姨还在,房间里的灰尘站不住脚。这就不是一段短暂的时间了。
那时候母亲说,小姨其实很难了,她的两个儿子,大儿子读完初中就不想读书了,成天不知道在干什么,小儿子很聪明,成绩也很好,但刚读到初三,就喜欢上和人去网吧、游戏厅,现在也不想读书了。
有天晚上,小儿子一直没回来,小姨冒着大雨出门,走遍附近村落的黑网吧和游戏厅,鞋子不知道丢在了哪座村庄,赤着双脚,揪着小儿子的后脖颈回来了。
母亲说,小姨被小姨父打得受不了,想带小儿子来南昌读书。不然,小姨父和大儿子都不做事,小儿子要是也这样,这一家就完了。
但是后来,小儿子也没有送来南昌,不知道哪一天,小姨突然就坐上班车回老家去了。她回去得那么突然,没有和任何人说一声,房间里的行李都没有带走。父亲母亲做好了晚饭等着她。母亲说,她能去哪呢,她又不认识路,总不会是有什么想不开?她打发我父亲出去寻找,找到半夜,小姨托老家街上一个不怎么熟的亲戚打来电话,说欢华已经回家了,那些行李,等以后有机会再来拿吧。
母亲这才提起筷子吃饭,一边吃,一边摇头,对我说小姨还是舍不得儿子,小姨真是不容易。
可是小姨留在房间里的东西,始终都没有来拿,起初说再来的,一直也没来。我母亲说送回老家去,小姨又还是不肯,说还是放在你家吧,说不定哪天还会来的。
但过去了很久很久,等到我成为一个青年,等到我去了异乡又离开异乡,小姨都没有再来。头几年,母亲留着她的床位,天气好时,会搬出被褥晒一晒,后来,就用大塑料袋封装起来,塞进衣橱里面,床板上堆起了杂物,房间里的事物上,灰尘一层又一层。住过人的房间又重新住进了杂物。母亲说,不来也好,反正再来也不会住在这里了,住好的地方,大房子。
3
小姨的两个儿子,一个比我小,一个比我大。小儿子是海军,大儿子初中肄业。
回老家之后很久,小姨都没有再来,但常和我父母打电话,问一问部队里的事情,问一问异乡的生活。母亲说,欢华还是想出来的,反正小姨父早晚都在外面转,现在屋子里,始终都是她自己,有时和大儿子在屋子里相对,从早上看到晚上。
但小姨还没有下决心出来,大儿子就说,要出去找点事情做。但走到县城,从长街东头走到西头,从南边走到北边,又走回了家里。他说想来想去,还是想种地。
但是没有地给他种了,老家是座小渔村,水面比地面多得多。小姨带着大儿子,在村里从东走到西,从南走到北。村干部说,你承包一座山吧,山上有柚子树。小姨带着大儿子,在“光荣之家”的金色牌子下点了点头。
那座山不高,石头比土多。山上原先就长满了柚子树,树被藤蔓缠得一层又一层,就像一个个巨人,披着军大衣,蹲坐在山上。村里说,这座山,要么你们看守着,别起火,别被人盗砍,一年下来,给你们五千块;要么你们自己收拾出来,柚子都是你们的,一年下来,给村里五千块。
小姨看看大儿子,大儿子想了想说,我们自己收拾。他每天清晨带上长柄镰刀,一棵树一棵树砍藤蔓,砍完一座小山头就泄气了,藤蔓太难砍,夜里挂在上面的蝙蝠,红着眼,胖得像小猪。
大儿子用积蓄在县城租了一间小店面卖水果。小姨给他说了个老婆。等小儿子退伍转业,就能苦尽甘来了吧。
但大儿子卖了几天柚子,就觉得没劲。县城没有多少人买水果,大家村里都有亲戚,平时走动,捎带的水果都能堆成山,谁还会来水果摊呢?大儿子坐在水果摊里不开口。大儿子躺在遮阳伞下打瞌睡。
小姨说,你不能这样等着别人来送钱,你要吆喝。大儿子闷闷的,比小姨还小姨。
小姨在电话里和我母亲说,嘎没有办法哦,赚不到钱也没办法哦,好在多少有个事情做,没有被街上的青年带坏。
我母亲说,儿子都有事情做了,你来南昌不?
小姨又说走不开,要上山种柚子,儿媳妇也要生了,等着带孙子。
大儿子从午睡中睁开眼,有外地来的客人在水果摊前喊了好几声。他迷迷糊糊没听清。客人走到隔壁水果摊,称了好几袋。
大儿子一下就清醒了,找到隔壁老板,说这是我的客人。隔壁老板呵呵笑,每一声都好像打在他脸上。
日头昏沉,再无一个客人。大儿子越想越气,再次找到隔壁老板。那人又是呵呵笑。好像重新把他打了一顿。
大儿子转身摸刀子,隔壁老板跳上车。大儿子发动面包车,追在隔壁老板身后。他也没想干什么,只是想把打在脸上的无形的巴掌扇回去。你追我赶三十公里,隔壁老板的车忙不迭,翻进临县的河沟里。
小姨在电话里说,你等一下,有人叫我。
我母亲就听见电话那边的本家老婶喊,欢华不得了了,你儿子杀人了,杀人了,杀人了!
小姨就撂下电话,跳上农用三轮车,慌慌张张往临县赶,天色越来越黑,开始下雨。小姨似乎想起了当年赤着脚,走遍附近村庄的游戏厅。她在白琥珀般垂落的暴雨中加速,避让车辆,翻进河沟。她丢下三轮车,手脚并用爬出河沟,向路过的每辆车招手。她截停了一辆皮卡,坐在车斗里,浑身发抖,来到临县的河沟。她看见大儿子蹲在河沟旁的公路边,一辆小卡车翻在河沟里,车门打开,里面没有人。
你杀人了?小姨站在琥珀般的暴雨里问。大儿子懵懂抬头,说没有,没动隔壁老板一个手指头,他被人拉出来,送进医院了。大儿子猛地站起身,好像见到了鬼。
小姨这才感觉到麻木下面的剧痛,她低下头,胸前衣服上全是血,黏糊糊,湿漉漉。她顺着鲜血往上摸,摸到脸颊边湿乎乎,软塌塌,什么东西垂下来,好像一块破布。她再往上摸,摸到了自己裸露在外的潮湿牙床和冰冷牙齿。她先前翻在沟里,三轮车撕开了她的半边脸,裂口延伸到耳朵边,面皮耷拉在下颌上。
小姨提起垂落的半边脸,捂在颊上。她站在自己的血水里说,你是要当爹的人,你要是发蒙杀了人,你的儿子怎么办?
4
小姨再来时已经像一块木头,脸上的褶皱变成一圈圈年轮。她坐在桌边,眼睛盯着桌子对面,双手放在桌子下。她的小儿子,当年那个雨夜被她赤着脚,从游戏厅提回来的孩子,现在是个退伍军人,坐在身旁为她夹菜。他夹一筷子,她才吃一口。
小姨是来看病的。
父亲说,不知道小姨是什么病,她好像什么病都有,但身体的每个部分偏偏都能运转,她又好像没有什么病,可整个人的气息已是肉眼可见的枯萎。听不见,没回应,不说话。
是不是癔症?只能往这方向考虑。有没有办法?还是要从心理疏导。
我们就都避开了这个话题。母亲和我说,小姨太不容易了,大儿子判了半年,水果店没了,车赔了,剩下一座荒山,柚子又苦又涩。小儿子在家待不住,退伍没多久,半条根已经扎在异乡了,找了一个女朋友,跟着亲戚创业,听说也不容易。
小儿子才攒下一笔家底,准备年底结婚,小姨就是这时候生病的。
起初是手抖得厉害——这是家族病,没有人注意——然后是时常叫不应,就像失了魂,只知道自己不舒服,怎么不舒服,不知道。在村里找仙姑看了,说是上辈子享福太多,这辈子来受苦了。怎么治?不知道。隔壁村的耶稣会闻讯而来,一个神父带着四五个姐妹,拉着她,说姐妹,受苦了,主会宽恕你的罪过。小姨的眼里有了点光。神父拿出一张信纸念了很多,说信主吧,信了主,我们陪你多说话,有什么事情都能来帮忙。
小姨接过十字架,颤抖着摆在堂屋桌上。
小儿子回家,给我母亲打电话。我母亲说,不要等了,带来看病。
检查做了一个月,报告单上,浑身都是毛病。小姨说,不要紧的,农村人都这样。我母亲说,你是吃了太多苦了,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了,儿子都长大了,是享福的时候了。
小姨讷讷地,点了点头。
我母亲说,长住下来,带你到处走走,玩玩?
小姨说不了,还要回去带孙子孙女呢。
小姨回去不到一个月,一个凌晨,她的小儿子打来电话,说小姨扑倒在床上,口吐白沫,浑身抽搐,已经叫不应了。
连夜叫车拉到南昌,直接住进ICU。医生说是脑出血。那补充凝血因子和血小板啊。医生又说,心肺乃至各大血管里都凝满了血栓。那用抗凝药啊。说完我父亲就哑然了,这是一个矛盾的死局,就像小姨这一生,一直都处在自我的纠结和矛盾当中。
在ICU住了七天,用完了能借到的最后一分钱。小儿子红着眼睛给每一个亲戚递烟,说没办法了,只能拉回家保守治疗了。
所有人都知道,这是小姨最后一次回家。她这一生从来没有走出过多远的路,一直在原地打转。原地,除了目之所及的日复一日,就是不断从她身上淌下的血水和苦水。
回家的第三天,小姨走了。小姨的走是一块小石子,丢进了整个家族的池塘,那些如池水表面延展的纱幔一样远赴的亲戚,被这块石子的坠落拉拢回原点。她老屋的邻居们大概都忘了,这个平日沉默寡言的女人也是有这么多亲戚的。停灵三日,车群阻塞,人流拥堵。
5
我到时,亲戚们已有很多,小姨的屋子住不下了,村里亲戚的屋子也快住满,后面来的只能住在县里,更远来的,在隔壁县落脚。
小姨的冰棺停在屋子的大堂,一面墙上是红十字架相框,两旁贴着红纸印刷的对联,也是基督教主题。下方的供桌上摆着小姨的照片,小小一枚,似乎是不久前照的,像个苍老的老太太。儿子一个在前屋,一个在后院,招呼突然从远方归来的亲戚。
我母亲坐在大堂,看着冰棺里的小姨发呆。父亲走出来对我说,去劝劝妈妈,两天没有合眼了,休息一下。我走进大堂,轻轻拍了拍母亲,她说没事,站起身扶着我的肩膀,来到小姨的冰棺前,对躺在里面的妹妹说,榕榕来看你了。
晚上,母亲、小舅舅住在二楼。冰棺已经断了电,小姨的两个儿子跪在大堂。
在外闯荡了半辈子的小舅舅回到老家后养过鸭子,不忙时也帮忙给人做“八仙”,时长日久,就成了村里经验最丰富的“八仙”。睡到凌晨三点多,小舅舅霍然坐起身,母亲睁开眼,问他怎么了。小舅舅说,要去给妹妹擦身子。冰棺断了电,夜深露重,小姨身上会结露落霜。人走的时候,要干干净净,清清爽爽,不能湿漉漉的。小舅舅“咚咚咚”地走下楼为小姨擦拭完,又睡了一个小时,又霍然坐起,说去给妹妹穿寿衣,年轻人不知道,这时候还要再擦一次露水。小舅舅又“咚咚咚”地走下楼,在基督的挂像下,这位“八仙”最后为小妹妹穿好临行的衣服。
天终于蒙蒙亮了,小姨已经穿裹妥当,移入棺木。我看见小姨父站在大堂,面无表情,微微垂着头,和熟稔的、陌生的亲朋打招呼。他的大儿子在前厅,小儿子在后院,给从每个方向、每个角落来的亲人发了一条白色的毛巾。人们走进大堂,绕着小姨最后走了一圈。她还是那么瘦,皱纹横生,可是她明明是这一辈里最小的那个。
亲朋们绕完了一圈,耶稣会的神父搬出一张方桌,六个人围坐一圈,开始为小姨做最后的祈祷。我们走出大堂,远远看着里面躺着和站着的人们。有更远处来的亲戚问,欢华什么时候信了基督?不知道。他们自己来的?不,重病的时候,她想找人说说话。
祈祷结束后,小舅舅招呼一起来的“八仙”上前封棺,用一条红毛巾盖在棺木上。“八仙”们固定好绳结,两边发力,缓缓抬起,周围一下子喧嚣起来,人们跟着往外走,队伍开始行进,向着最后发丧的码头而去。
我跟在母亲身后,看见她、大姨、大舅舅、小舅舅,除了十年前离世的二姨,他们兄弟姐妹互相搀扶,跟随在行进的棺椁左右。大舅舅披着毛巾,走在队列的侧前方,边走边侧目,鬓发霜白。小姨的两个儿子披着麻布,走在棺椁的正前方。后方是绵长的队伍,像一段缓慢流淌几近凝固的铁,不可阻挡,也没有尽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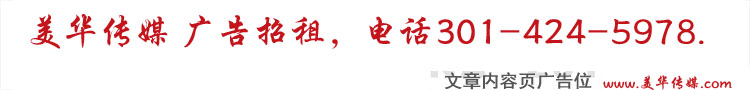
 相关文章
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
精彩导读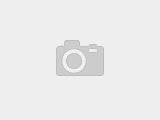



 热门资讯
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
关注我们
